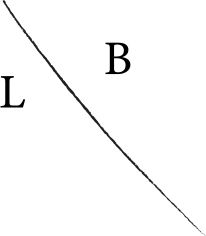陆斌那些无畏的化石(节选)
[美国]格伦·R·布朗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艺术史教授、著名艺术批评家
(原载美国《陶瓷月刊》2006年6月号)
对于考古学家们而言,长久以来,陶瓷一直是古代器物中最有说服力的,而且,尽管过去数世纪以来,诸如塑料这样的新材料不断地被引入技术领域,但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假设陶瓷作品应当从此不再是具有特别意义的记录文化的载体。陆斌曾这样写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陶瓷一直在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不同的环境,并且为以后的学者详尽地描述它们所处的那些年代。中国古代的陶瓷,如汉代的砖瓦,唐代的三彩釉陶,明代的青花瓷,等等,所有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陶瓷艺术风格中每一次巨大的变化,它们将历史与文化联结在一起,都与重大的历史变革密切相关。正如清代学者朱琰所说:“因器而知政”。
陆斌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一观点,因为他自身的经历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生于1961年,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迫于政治性的强令,全家人从北京迁居中国西南部偏远的贵州山区,如果不是因为毛的去世和邓小平推行更开放的政策而带来的政治变革,他或许根本不可能走上陶艺这条艺术生涯。从贵州移居南京,他是南京艺术学院陶瓷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在这里他于1988年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师从潘春芳——一位传承宜兴传统的紫砂壶大师,因而,他不仅掌握了传统艺术造型,更掌握了严格的创作技法。他也逐渐了解到一种新的艺术运动渐渐地开始在中国陶艺界兴起,这场运动正在打破宁静,并对传统提出了诸多诘问。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西方社会的态度的日趋温和,现代主义流派中的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甚一日。正如孙振华博士所写到的那样,“这一时期陶瓷界中的最主要词汇就是“叛逆”和“语言”。那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传统陶瓷造型桎梏的反叛,以及后期将陶艺列为实用艺术的一个门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确立一种陶瓷语言,而这种语言则是表现性的、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且与众不同。”陆斌和一群整体上被称之为“第四代”的其他青年陶艺家们一起,开始探索陶泥中一切可能的表现形式,而陶泥在当时并不是己有的所有艺术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创作的这些作品,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雕塑作品,如《活字系列》、《城市系列》、《砖木结构》,以及目前创作的《化石》等,不应被描述为纯粹的形式主义。陶瓷化石的寓意及其与曹雪芹《石头记》吻合,就一直清楚地表明长期以来陆斌对陶艺作品所进行的思考。曹氏小说的环境就是古代的南京城(因其是在公元三世纪吴国统治者孙权的城堡上的废墟上建成的,因此,也被广泛地称为“石头城”)。虽然陆斌早在他在南京艺术学院接受新职位之前,2000年初就开始了他的化石系列,但他已经在思考这些废墟的象征意义。他说:“今天,那座古都早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则是历史的遗迹和城墙的一些残垣断壁。城墙的一部分是用砖和石修建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将它们区别开来则十分困难。”
当然,这种差异并非主要表现在视觉上:它存在于石与砖所构成的不同的条件之中。前者是自然变化过程的结果,因此,最初就是地质变化的结果。只有当用人的双手完成造型时,它们才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更似文化产品,而非自然的形态。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砖同其他陶瓷艺术形式一样,从根本上讲具有文化的内涵,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人既无法逃避作为文化存在的环境,也无法将他们的行为与确定这种文化概念和形式的环境割裂开来。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陆始终清楚地懂得,他或许是采取目前甚至无法感知的创作方式,用陶泥创作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影响着他的这种文化,正因为如此,它们注定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描述今天,恰如终会有一天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段遥远的,且记忆模糊的历史时期的那些化石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陆斌最新创作的作品中,那些表面上看去犹如化石的作品不仅包括那些自然的和没有特定时间限制的造型,例如鱼和水果,而且还有那些完全属于当代的艺术造型。从某种程度上讲,陆斌对某种角色的认定,即他的作品将最终会成为带有文化意义的化石,就会使他对内容的选择表现出一种责任感。在中国国内,工业领域日益加深的痛苦和不断高涨的消费主义正在震憾着今天的中国,在国外,全球社会的快速和无情的发展令中国感到不安。当今中国的文化变革完全象半个世纪之前文化大革命中的剧变一样充满了戏剧性,对陆斌而言,他的作品应当面对这样的艺术运动,而不是长久不变地保留这些传统的陶瓷造型,躲进往日的宁静之乡。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文化和历史,传统和现代等诸多问题。”他认为,“回避因这些问题而形成的挑战是懦弱的表现。这些能够大胆地记录当代人的困惑和痛楚的艺术作品最终会有机会陈列在未来博物馆的玻璃橱窗中,因为它们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持征。这样的结果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石头记》的主题上。世界上的一切如浮云一样转瞬即逝。最伟大的财富最终都会变为一块记录某段时代烙印的‘化石’。”
对未来的这种幻想——只能通过沉溺于今天和摆脱昨天才能完全实现自我——就是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一种象征。在一个国家中,或许最正当的和最有效的视角就是见证诸如此类瞬息万变的文化变革。尽管陆斌或许主要关注的是内容,而不是审美形式,然而,对于他的论点却有一个无可辩驳的前卫特征:只有摆脱以往经典艺术的规则,才能获得使其自身成为未来经典的潜力。陆斌写到:“从作品的形式上来讲,我的作品背离了传统陶瓷艺术。透过当今的氛围,我的雕塑作品从根本上讲已经不是传统陶瓷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那些超前的陶瓷艺术都必将成为明天的传统陶瓷艺术。这就是对我的作品的希望。”